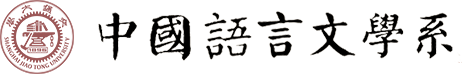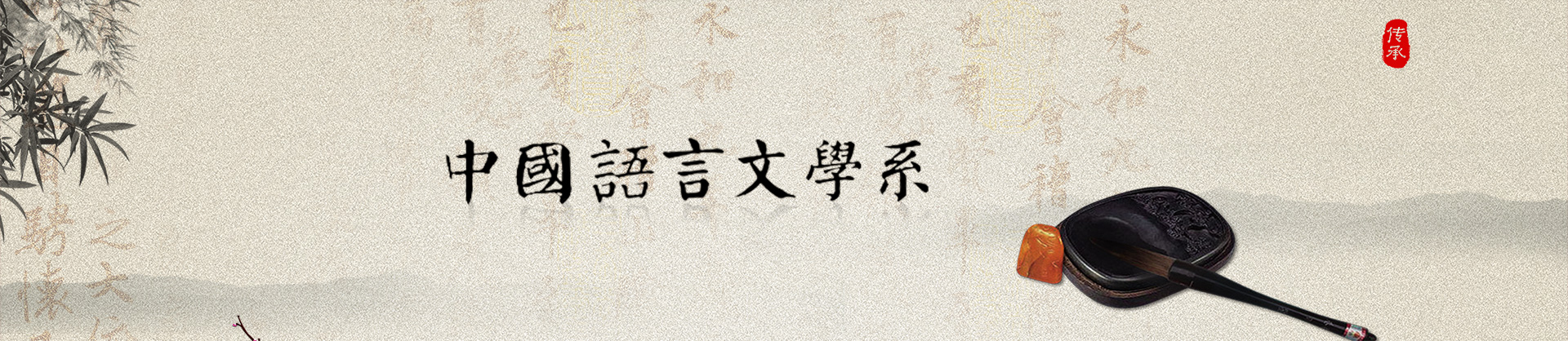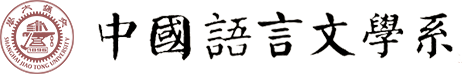《文艺研究》王杰、徐方赋:“美学、社会、政治”——托尼•本尼特访谈录
“美学、社会、政治”——托尼•本尼特访谈录
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著名社会与文化研究专家,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研究员,现任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社会与文化研究教授、墨尔本大学任文学院客座研究员;此前曾任英国开放大学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中心主任、澳洲文化域媒体政策重点研究中心主任。本尼特著述颇丰,主要集中在文学与美学理论、文化研究、批判性博物馆学和文化社会学等领域。2009年5月本尼特应邀赴南京参加“文化研究关键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于5月12日接受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王杰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语系徐方赋教授的采访,就美学、社会和政治以及民族与习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现将访谈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王杰非常高兴您专程来南京参加这个学术研讨会,我们翻译的您的Culture and Society(《文化与社会》)中文版出版后,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已经有多篇学术论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您的著作。这表明中国学术界对您的研究和著作越来越感兴趣。兴趣点之一在于您早期对卢卡奇笔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所以能否请您先谈谈您早年的研究背景以及这种研究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关系?
本尼特我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兴趣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我的学术道路并非开始于文学艺术和美学,而是开始于社会科学;正是这一背景为我后来开展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我从牛津大学获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从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获文学硕士,专业方向为文学中的社会学,正是在攻读这个硕士学位的时候,我首次对卢卡奇的著作产生了兴趣,而且这一兴趣一发不可收,一路引领我一直到我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直接就把选题确定为研究卢卡奇的文学现实主义及其关于阶级意识这两个概念的关系。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那个年代里,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人们对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趣倍增。阿多诺、本雅明、葛兰西和卢卡奇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纷纷译成英语,在英语国家,人们如饥似渴地研读这些著作、并展开热烈讨论;而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早年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被译成英语并广为传播,这部著作代表了马克思历史美学和人文美学的萌芽。随之而来的是,诸多非正统的解释融入了新左派的理论和政治,英语国家的知识分子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表现出巨大的兴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大批左翼知识分子对卢卡奇的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要原因在于苏共二十大以后卢卡奇在苏共内部开辟新的批判领域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他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及此后在短命的纳吉政府中的作用,再如卢卡奇1956年的著作《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Realism)对正统文学批评理论所提出的挑战等等。我接触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只是后来的事情,因此我对卢卡奇著作的兴趣并非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的诠释。我刚刚提到,我对卢卡奇著作的兴趣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他在上世纪30至50年代发展起来的文学现实主义理论,另一个是他1923年的早期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中所提出的阶级意识理论。我在阅读《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发现卢卡奇运用了黑格尔的方法:他将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层面体现了历史的自我意识。同时,卢卡奇认为,人类历史中辩证法的作用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这些观点在那个时代颇具魅力;只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衍生出一种历史和哲学立场,并使人类最终理解其自我发展历史进程的整体性;在这一进程中,无产阶级同时既是客体、又是主体(即作为历史发展产物的无产阶级,能够认识到自身在历史进程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必然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尽管现在看来,我认为这些观点很成问题;但在那个时代,这些思想十分令人鼓舞,因而其深受当时胸怀理想的青年学生们所喜爱,也就可以理解了。不过具体地说,我那个时候所做的研究主要遵循两条轨迹,一是探索卢卡奇的文学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尤其是从批判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如何遵循一个基本一致的理论框架;二是搞清楚卢卡奇在苏联期间,如何能够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将批判哲学融入于自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因为一般地说,批判哲学同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很不相容。
对不起,我说得有些多,但这些都是在英国新左派接触和熟悉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卢卡奇著作激发我研究兴趣的诸多方面所在。
徐方赋那么除了卢卡奇,您的研究还受哪些人的影响呢?
本尼特这是我正要接着说的问题。尽管卢卡奇的著作在上世纪60年代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久便趋于消退,原因是随着当代法、德、意等国家的社会理论译成英语后大量传播,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持批评态度的各种学术思潮,均对卢卡奇理论赖以产生的前提提出了质疑。其中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大概要算路易•阿尔都塞,或者说阿尔都塞学派。尽管之前我对卢卡奇的著作怀有极大兴趣,但很快我就发现,无论是卢卡奇还是他所代表的黑格尔和人文主义方法,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走入了死胡同。阿尔都塞对这些传统理论的批评从诸多方面动摇了卢卡奇学说的基础。阿尔都塞将卢卡奇等人诠释马克思主义时所运用的概念称为“表现式整体性”(expressive totality)并加以批判,这种批判给了卢卡奇学说以毁灭性的打击,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卢卡奇看来,社会整体性由某种形式的社会整体所左右、由整体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所表达、并通过其所属的社会整体得以实现。而在阿尔都塞那里,构成社会形态的各个层次和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关系,从而展示了更加灵活的可能性,因此卢卡奇的这种“整体性”便告破裂。这并不是说阿尔都塞学说主要针对卢卡奇理论;但是我们能够明显看出,阿尔都塞的观点确实适用于对卢卡奇著作的批判。与此同时,卢卡奇观点的政治局限性亦日渐凸显。刚才说到,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成为历史主客同体的观点在当时看来颇具魅力,但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观点从根本上看无异于无产阶级自身的期盼,它试图在马克思-黑格尔理论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一理论体系本身的逻辑性有待进一步完善。卢卡奇试图通过满足无产阶级需求赋于其解决历史矛盾的重任,而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认为,这一逻辑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种政治倾向,而且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所激发的政治热潮中,很多卢卡奇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实际上,卢卡奇赋予无产阶级的这一历史重任只有哲学意义,舍此无他。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的理论更多地关注无产阶级本身的观点,而不是历史的现实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事实上,他的著名概念klassenbewusstsein,即“强加于身的阶级意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应更多地从哲学层次关注工人阶级本身的意识,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有这个愿望,实际上却没有做到。
徐方赋这是否表明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实际应用价值不大?
本尼特不是说应用价值不大,而是应用范畴不同,这个区分很复杂。不过在当时,将卢卡奇理论应用于对共产党和普通群众关系的讨论,确实为列宁主义的观点提供了精到的哲学解释:由于共产党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并正确了解其历史利益,因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违背工人阶级的意见和意愿也可能是合理的。
然而,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文学和美学问题上来,阿尔都塞理论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而且我发现这种方法较之于卢卡奇的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美学更有意思、更有活力。这一分析方法部分地由阿尔都塞本人所创立,尽管他只在两三篇文章中简单地提到,而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其合作伙伴的皮埃尔•马歇雷(Pierre Macherey)则对这一方法进行了充分发挥。在阿尔都塞看来,他本人关于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论述为研究文学和美学问题开辟了全新的方法。当然,卢卡奇也有其分析方法,在卢卡奇那里,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不同于其他二流作品,他认为,此类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其能够表达进步社会阶级的世界观,这些作品对人类在社会结构中作用的再现使其能够在某个特定时期表达最高层次的历史自我意识,从而区别于统治阶级片面而带有限制性的艺术视角,即意识形态视角。
阿尔都塞对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法。简而言之,其观点可大致表述为:文学艺术作为观察意识形态作用的一种途径,将意识形态的作用过程呈现于世、供人评判、使之为人可见,从而使意识主体有可能摆脱意识的束缚。不过与此同时,阿尔都塞同样关注如何将文学艺术同科学区分开来,如同将其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一样。他进行这种区分的基本方法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科学(显然指马克思主义)让人们了解意识形态如何通过一系列概念发挥作用,而文学艺术则让人们能够观察并强化意识形态的这种作用,从而使我们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可以描述为一种产生“主体”的机制,能够让人们各归其位、赋予其以不同的身份,从而使其认识到自身属于某一群体中的成员:这个群体可以是某个阶层、某个民族或者是整个人类。由此可见,
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卡奇以人为中心的美学理论将美学看成人类进步和发展历史中一种既成的、符合某一阶段特点的自我认识范畴,在阿尔都塞看来,卢卡奇学说本身即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这种美学同样是一种产生“主体”的机制,即运用“主体中心”的历史过程发展理论,根据一定的归类方法,将不同人群定位于某一群体和身份。
因此,我们又可以认为,不管卢卡奇出于何种兴趣和目的,其美学理论在当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我这样说并非要表明阿尔都塞的文学艺术和美学理论没有任何局限。我开始接触阿尔都塞著作的时候,同时还对俄罗斯的形式主义理论家产生了兴趣——这批20世纪初文学理论家的著作代表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学和电影理论,在70年代引起了广泛兴趣。我同时阅读这两类著作,惊奇地发现,阿尔都塞关于文学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同俄罗斯形式主义理论家关于文学作为一种“陌化”实践(a practice of defamiliarization)的观点惊人地相似。这些形式主义理论家认为,所谓“文学性”(literariness),即文学文本中关键性和区别性的效果在于设法使更早时代的传统文学表现形式显得陌生和久远。他们将文学看成陌化早期形式、开辟看待世界新时空的一种形式。诚然,这种关于“文学性”本质的观点同阿尔都塞把文学看作摆脱意识形态歪曲作用的一个机制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两者却有很多相似之处,我的第一部著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Formalism and Marxism)就是研究其中的相似性。
无论是阿尔都塞的观点还是俄罗斯形式主义理论家的观点都十分富有创造力,而揭示两者相似性的作用在于,前者的观点被诠释为现代文学美学的一个最佳流派,而该派美学恰恰是后者首先运用严格的理论概念加以清晰表述的。与此同时,对两者相似性的研究还揭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努力可能是徒劳而错误的,实际上这种努力同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革命性思想体系的说法并不一致。对此,阿尔都塞着重指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思想体系,这就意味着其历史使命不在于运用新方法解决旧问题,而在于提出新的问题并从理论上加以解答,从而取代以往各种资产阶级理论。否则,马克思主义者就无法自圆其说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开辟了全新的科学视域(在阿尔都塞看来即历史视域),相反,我们只能说,马克思主义只是针对资产阶级哲学所提出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新的解决方案。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各种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流派所做的全部努力。康德的《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依然是西方美学的主要著作,而我们从中找到了什么呢?我们从中发现,康德力图将审美看作一种特定的判断力,借以区别道德判别能力和学术判断能力,康德将每一种能力(判断力)解释为人类认知活动的不变模式。然而,这样一种非经验的、超验的方法,这样一种主体认知的不变模式,如何能够同以激进历史主义为基础、抱有革命性科学志向的方法相一致呢?
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革命性远远不及其倡导者所言。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学的理论在哲学上和理论上基本上属于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做的努力,几乎都集中于将美学同科学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将三者视为人类认知活动的三个普遍模式。所以,这种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框架等同于康德美学的理论框架。事实上,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同流派之间的区别在于各自引用不同的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概念,用以佐证自身方法和特点。因此我们有了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美学(卢卡奇)、有了康德派马克思主义美学(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等等,同时我们还有更接近于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美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流派(阿尔都塞)。此外,所有这些流派都将美学视为一种脱离历史过程而不变的观察和判断形式。
对于这一理论模式中的学术取向我有不同看法,因此我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的《文学之外》(Outside Literature)两部书中做了两件事情。首先,我对其中旨在将美学的区别性特征描述为人类观察和认知不变模式的各种研究的有效性提出怀疑,指出需要明确美学的定位,将其看作一种特定的判断力形式、一种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能力;第二,我认为即使运用以上概念建立美学理论并将其区别于科学和意识形态,那么,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任务也应该关注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使这种独特的美学理论产生一定的效果。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有很多理论家,这些理论的思路即使不完全相同,也十分相似,最著名的代表也许是皮埃尔•马歇雷。我想这些理论实际上都源于阿尔都塞主义理论,因为阿尔都塞十分清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范畴和分析方法均依赖于其试图超越的以往的思想体系。
王杰您的分析很有启发。福柯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了一定的美学因素,但不存在一种称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对此您怎么看?
本尼特我不大清楚福柯具体在哪篇著作中提出这个观点,但我认为这个说法的两个方面无疑都是正确的。刚才说到,整个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都显得困难重重,因为这种努力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之上。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政治理想——即设想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王国,其基础来自由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所带来的、对必然王国限制的历史超越——实际上是对康德和席勒关于美学属于自由发挥范畴理论的一个特定历史解读。但我发现福柯本人对美学问题的论述似乎有些让人莫名其妙。他的早期著作中广泛地讨论美学问题,比如说他研究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和雷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文章都不乏对美学问题的研究。不过在我看来,福柯对美学问题的研究没有超越同时代其他法国学者研究文学和美学问题时所运用的概念。而且可惜的是,在他后来宣称自己改变了学术研究方向后,再也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有影响的持续研究。他关于知识考古学的理论、在性史研究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对权力技术和自我技术之间关系的关注、他关于政府性、尤其是政府及其同自由之实践的关系等问题的著作等等,所有这些研究同他早年关于美学的论述均有很大差异,至于这些差异他本人怎么看待,这些差异对美学问题有何影响——实际上他自己是否想过这些问题——我们都不得而知。
但也有例外,主要是他在研究康德和有关启蒙运动著作时发展起来的“存在美学”概念,以及他对批评和自由之实践关系的阐发。不过这两个理论并不讨论传统上专属于文学和艺术的美学理论,而是研究日常生活的各种方式无论通过艺术还是其他途径而产生的一种批判性关系,即日常生活可以创造性地集中反映自由观念指导下的自我改造行为。
所以说,“存在美学”同关于审美只存在于天才艺术家创造的伟大艺术作品之中的美学理论风马牛不相及。既然如此,福柯的美学理念依然没有跳出康德理论的框架。康德认为,审美的作用在于它能够使人的各种能力达到自由协调;而且我不清楚福柯对于美学和自由问题的研究方法同他研究其他知识在构筑自由中的作用时所运用的概念是否一致,他认为其他知识所构筑的自由有助于实施自由政府产生的各种权力。
王杰有的人认为福柯和布尔迪厄都属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您是否也这么看?
本尼特福柯的情况很清楚,他毫无疑问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不知道他本人是否明确地表达过这个意思,但他的很多著述都表明他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诸多重大的概念性缺陷,同时他明确表示,他的关注焦点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而并非要从整体上采取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所以福柯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工人主义”因素(强调阶级斗争中工人重要作用的观点)提出批评,因为他所关注的很多政治问题,比如性别问题、囚犯权利问题等等都无法从阶级政治的视角加以理论上的说明或解决。作一个进一步的概括,可以说福柯的《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对他认为马克思思想中不合时宜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批评。比如说,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理论在福柯看来只是19世纪众多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流派,没有超出李嘉图关于劳动的观点。在后来的访谈和文章中,福柯还表示,他认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分析的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根本错误的。他在对阿尔都塞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中明确指出,他认为将意识形态看成主体中心从而同科学相区分的思想一无所用。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福柯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中将真理和谬误截然分开(the binary distinction)的思想,他认为这种区分无助于他所谓的真理政治(the politics of truth),即存在于特定知识体系之中并通过这些体系起作用的权力形式。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始终如一地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主体机制发挥作用,而且始终区别于他称之为科学的知识形式,这种形式可以脱离主体;而在福柯那里,真理与谬误之间、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并不存在像被中国万里长城隔开那么大的区别,福柯更强调具有社会意义的知识体系如何作为真理发挥作用的工具在社会上产生具体而真实的权力效果。
因此福柯同阿尔都塞或者说马克思的思路完全不同。与此同时,我早年研究卢卡奇时就已经发现,卢卡奇和其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文主义解读时提出的人本思想(man-centered structure),福柯亦予以坚决反对。在这一点上,福柯的观点又同阿尔都塞的反人文主义理论大有相似之处。马克思将历史看作人类发展过程的人本思想以及黑格尔和卢卡奇美学中的人本思想man-centeredness,福柯都持有异议,他认为,必须通过考察使“人”成为知识客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话语机制的相对变化来取代人文主义思想。
徐方赋既然福柯对人本主义提出批评,那么他有没有提出自己关于美学应该以什么为中心的观点?
本尼特没有。福柯及其同时代理论家们所持有的鲜明观点是,我们不能将历史解读为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过程,历史只能解读为非连续过程,而不是连续的过程。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诚然,这个连续过程之中会有革命产生的断裂、会有深刻危机的产生、甚至会有倒退,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种种断裂的背后,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生产能力的稳定发展构成的永恒动力推动着历史整体过程永不停息地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前进。福柯反对这一逻辑,他将历史看成一个不连续的过程,因此他同样反对关于社会各组成部分均属于某个统一的权力中心的观点。这一立场成为后福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成为了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著作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很明显德勒兹受到福柯的很大影响。
福柯认为需运用“玄主体化”方法(de-centred approaches)重新分析权力的理论最为简明的表述体现在他的一句口号当中,即我们需在政治理论上“砍掉国王的脑袋”,也就是说,在研究权力时要有新的思路,不要以为当今社会条件下权力的组织依然等同于西欧历史上的绝对君主制度,这一制度中权力集中于君主。所以在福柯看来,君主权力作为一种特定的权力组织形式是同西欧历史上专制政体相联系的,在这一政体中权力集中于一点,即君主;这并不等于说当今社会中君主权力已经完全被其他权力组织形式所取代。实际上,“砍掉国王脑袋”的政治理念指的是不再将君主权力当作唯一的权力组织形式,反言之,应该认识到权力的存在呈现多元化趋势、权力的运行呈现多渠道趋势,这一理念同样同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区别。在福柯看来,当今社会中权力作为资本权力的政治表达,并不集中于资本或者国家。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或资本对于权力的组织和运行无足轻重,而是说两者并非仅有的权力中心。
在这个问题上,福柯关于“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论述尤为重要,因为其中首创性地分析了通过不同知识体系起作用的不同权力形式,尤其是同人口管理相关的权力形式。这也是福柯早期著作的关注焦点之一。比如,在《疯癫与文明》中,他指出,要了解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社会对待被称之为“疯人”的新方法,就得考察由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法等构成的知识体系如何通过各种途径在其特定机构(如疯人院等)中发挥作用,以其特定的方式将“疯癫”作为一类问题加以表征,因此产生了一批专家。诚然,福柯承认对待疯癫的方式的发展同各种经济关系组织相应变化是有联系的;但他同时认为应将这种发展视为独立的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同其他历史活动的交错关系应予以具体剖析,而不应只是进行先验和笼统的理论概括。新型医学权威和技术的发展同区分和管理“疯人”方式的发展密切相关,而考察这种发展应将其视为独立的知识和权力范畴、依据其自身的理论体系独立进行。我的观点与此类似,即尽量把文化分析同意识形态的复杂问题区分开来,认为文化是由不同知识体系和技能构成的范畴,并用来管理人们的行为,而这种管理的具体途径不能简化为某种统一的国家概念或者经济活动的要求。
徐方赋那么布尔迪厄呢?他是否也是后马克思主义者?
本尼特我想布尔迪厄同福柯一样,也没有明确表示他自己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在很多方面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在布尔迪厄那里,社会阶级问题依然是其著作的核心。福柯很少探讨社会阶级的问题,也很少谈到在当今社会不平等形式中,阶级起了什么作用。在《必须保卫社会》(Society Must Be Defended)一书中,福柯确实谈到了阶级,但只是从历史的视角关注西欧各国历史上“阶级”、“种族”和“民族”的划分如何相互重叠和交织;同样,在其《生命政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一书中,福柯探讨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社会排斥的政治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造成社会不平等之根源的道德分析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是在探讨这些关系的过程中,福柯对“阶级”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与此相反,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阶级”则是贯穿始终的中心焦点,从他早期关于教育社会学的著作,到他关于阶级和文化的名著《区分:对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一直到他后期关于住房问题的著述,他的研究始终没有离开阶级的视角。同时布尔迪厄还运用阶级视角研究文学艺术的发展。但是请注意,布尔迪厄研究阶级问题的思路并不一定采用马克思的方法。他将阶级看作是一种文化结构群体,而不单纯是由经济决定的职业群体,这一观点实际上更多地受到了麦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影响。布尔迪厄不是将阶级矛盾看成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更多地关注由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带来的不平等的人生机会。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他关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决定人生机会中起不同作用的论述中。布尔迪厄首创的核心概念“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主要关注人生机会的不平等如何得以延续和传承,这种传承的原因在于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人们,由于熟悉为教育制度所认可和褒奖的各种文化知识和实力,有能力将自己的特权和资产(比如教育资产和优势)传递给自己的子女。基于此,中产阶级的子女们在学校里往往比工人阶级的子女更加优秀,他们有更多机会上大学并有上乘表现,同时毕业后更有可能进入地位高、薪水高的中产阶级行业和管理岗位,这样,中产阶级就成功地将文化资本传给了自己的子女,从而开始了另一个传承循环。
徐方赋能不能这么理解,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孙打地洞”,这个话听起来有些土气,但好像符合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传承理论。
本尼特哈哈,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大致概括。而且你可以看出,布尔迪厄十分重视阶级的概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十分信奉阶级政治:同福柯一样,布尔迪厄对各种试图以工人阶级利益为中心协调所有社会斗争的观点持批评态度,并且经常对工人阶级的局限性提出尖锐批评。他反对“工人主义”。这就是说,在法国各种产业活动中,他经常支持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运动,但他不像卢卡奇那样支持工人阶级的一切言行,卢卡奇认为工人阶级(在理想状态下)可以成为真理的源泉,而布尔迪厄并不这么认为。比如,在关于殖民政治和移民政治等许多问题上,布尔迪厄强烈地反对法国部分工人阶级反移民的立场和观点。所以说,布尔迪厄的大部分实证性研究都没有将工人阶级理想化,而是致力于揭示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机制如何令工人阶级陷入严重贫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条件,同时布尔迪厄同样致力于揭示产生和传承特权的各种机制。
徐方赋您的分析让我们深受启发,接下来能否谈谈您学术兴趣的发展,也就是说您最近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本尼特过去三四年中,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课题,一个课题是从布尔迪厄那里受到启发,而另一个课题则采用福柯的思路。第一个课题是一个集体项目,我同开放大学和曼切斯特大学的很多同仁一起从事这项研究,内容是通过长期和大规模实证调查,研究当代英国社会各种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阶级关系的组织形态。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刚刚由英国Routledge出版公司出版,书名为《文化、阶级、区分》(Culture, Class, Distinction),本书详尽考察了当代英国社会中阶级、文化资本和特权传承机制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些内容;同时,本书还研究了年龄、性别和民族性等因素如何使以上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当然,我们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对布尔迪厄的主要理论概念,比如习性、文化资本和场域等等(habitus, cultural capital, and field)也展开了研究,以探讨在当今社会科学理论框架下这些概念有哪些需要修正的地方。其中我尤为关注的一个方面是布尔迪厄关于康德式的“无功利”审美(the Kantian aesthetic of disinterestedness)和“必然品位”的工人阶级文化(1)之关系的论述,以及这一论述作为美学与社会实践关系的一种历史学说所起的作用。布尔迪厄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然富有创新,但其局限性亦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因为他仅仅将美学理论和实践同阶级不平等相联系来考虑问题,以此研究美学理论和实践的社会表现(the social inscription of aesthetic discourse and practices),而如果我们从治理实践的角度来研究美学理论和实践的作用,则会展开一个大不相同的社会和政治历史视觉。
当然,研究美学和治理性的关系可以有不同的方法,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著作就提供了一种研究视角,我发现有些用处,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福柯关于自由政府(liberal government)的著作中为研究美学历史和治理性实践的关系所提供的视角,这个视角即构成了刚才说到我的第二个研究课题的部分内容。该课题取名《构建文化、变革社会》(Making Culture, Changing Society),核心即研究福柯的治理性理论对文化研究具有何种影响和作用:即对此如何进行界定和研究。比如,不同形式的文化技能和知识同福柯所称的“行为管理”(the conduct of conduct)的组织有何联系?这些知识和技能在构建不同形式的文化中发挥何种作用?所构建的不同形式的文化同不同人群行为的管理有何联系?不同形式的文化同社会积极行为之间联系的机制是什么?这些文化形式具有何种改造或者调节的效果?所有这些问题旨在分析诸如美学、历史、人类学、社会继承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等等不同的文化知识体系如何在特定的机构环境中构建不同形式的文化,这些机构包括博物馆、艺术馆、电台、电影院等等,其本身同社会积极行为的关系各有自己的诠释。
运用福柯关于自由政府的理论来研究这些问题,意味着我特别关注文化在构建和组织特定形式的自由中的作用,而各种形式的自由政府则通过自由的这些形式得以运作。本课题同样是一个阵容强大的集体项目,合作者是我多年来一直共事的开放大学社会文化变革研究中心的同仁们,这个中心由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资助,今年我晚些时候我将赴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任职,此前我将继续和这些同仁们一起工作;同时参加该项目的还有我在开放大学的同事Francis Dodsworth,曼切斯特大学历史学家Patrick Joyce,以及伦敦经济学院的社会学家Nikolas Rose等等,我们在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统一组织下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讨论会,主题为“政府和自由:历史和未来”。在整个大项目中,我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文化知识和技能各种具体形式的社会分布如何构成最好称之为“自由文化技术”的各个组成部分,这些技术从根本上作为一种工具促使人们积极地、自由地参与监督、调节和改变自身行为的过程,而且这种监督、调节和改变的方式同政府特定理性规范的要求相吻合。根据福柯的自由政府概念,自由成为政府的核心理念和组成部分,即成为一种治理机制,那么文化在生产自由作为一整套技术得以体现的齿轮和机器中起到何种作用呢?这种自由,当然不是自由哲学家们所议论的自由,而是一整套社会和物质技术和条件组成的自由。
我和课题的合作者正是根据福柯的理论,通过这样一个视角来研究美学的。当然,将美学和自由相提并论并非我们首创,康德才是首创。但我的研究主要在于搞清楚这种相提并论如何构成由物质、机构和话语技能组成的独特历史的一部分,这些技能为艺术作品、及其生产者和使用者所运用,构成了某种形式的自由,而这些自由形式形成了独特的治理形式。当然,这种研究需在一个更广阔的研究视野中才能进行,也就是说,我们同时要研究美学作为一种特定技能,在生产和分配自由机制支配下的自我管理形式方面,如何同其他形式的文化技能(如历史学、人类学等等)既相辅相成、又有所区别?所有这些文化技能作为文化知识的具体形式,通过各种独特的行为方式,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并产生影响,从而通过博物馆、继承性机构和社区艺术实践等等各种复杂的机构体制以不同方式改变着社会行为。我说要将美学研究放在一个广阔的视野中,当然是在西方美学理论,尤其是康德理论的框架下,探讨从美学视角思考和构建艺术作品及其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王杰是的,不过您的分析是基于西方语境。我在昨天研讨会上也提到,在中国,关于美学问题的思考语境大不相同。以博物馆为例,中国和英国都有很多以战争为主题的博物馆,但通过博物馆表达的理念却有很大差异。中国的战争博物馆大多表达英雄主义主题;我们在英国也参观了不少战争博物馆,例如曼切斯特的帝国战争博物馆,我感到这些博物馆表达的主题更为多样化,更为关注战争的残酷性和毁灭性。
本尼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您指出,英国的战争博物馆不同于中国,而是更加注重表现战争的残酷性和毁灭性,这是当下博物馆表现的主题,应该说这一倾向的历史并不很长。比如您提到的曼切斯特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刚刚建立时候也是大肆歌颂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英国英雄主义和军事实力。后来对战争的歌颂逐渐减少,但并没有消失。从60年代开始,英国和其他很多西方国家的博物馆才真正减少了炫耀民族主义情结的元素,眼界更加开阔,开始以一种审视的态度来看待战争、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这种变化是当时博物馆因遭到多方批评(比如种族政治学)而变得更为开放。而如果你在上世纪50、60年代去参观英国、美国或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博物馆,你可能会看到其中的展品着力表现的理念就是西方人在本质上比其他人种更为优秀。如果说现在情况不同了,部分原因在于所谓“新博物馆学”的发展。“新博物馆学”根据当时博物馆面临多方批评的形势、吸收了众多学科的最新发展,对早期博物馆的理念以及关于种族关系、性别关系等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检讨。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博物馆学”是对新左派运动的一个回应——新左派运动抛开原先只注重阶级政治的立场,同时关注种族政治、性别政治和民族政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原先的博物馆成为了政治激进派的众矢之的。女性主义者聚集在博物馆前、甚至冲到里面,抗议博物馆把妇女描绘成男人的附庸,只是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如此等等;与此同时,英、美国内的博物馆还受到来自非裔美洲人强烈抗议,他们批评英美博物馆抹杀非裔美洲人的文化、并且一直将非裔美洲人描绘成劣等种族,如此等等。这些政治运动产生了仍在变化发展的博物馆政治学,不但影响了“新博物馆学”,而且对其他学科的理论也产生了影响,比如文化研究和社会学,而这两个学科为人们理解博物馆同社会和政治过程的关系均做了大量富有创新的重要工作,这些工作体现在目前的大学课程中,为博物馆长和其他博物馆工作者提供培训,以使西方国家的博物馆业者熟悉这些问题并保持敏感性。
以上情况表明,在当今条件下,博物馆成为了运用新型文化知识和技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社会变革的场所。当然,早期历史的残余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卢浮宫等机构总是认为其作为可作全球性调查研究之用的博物馆,从理论上说能够满足各国文化素材回归本国的需求,这些文化素材,如埃尔金大理石(3),比置于其原所在国具有更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和价值。这种观点显然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现在回到您刚才的问题上来。如果能够看到中国进一步开放,使文化研究等学科接受引入批评视角、博物馆行业引入“新博物馆学”,并推动以博物馆作用为主题的类似西方的政治性探讨,那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通过这样的讨论,学术界和社会活动家们可以一起努力,推动改变知识和权力的关系。
王杰这里面还可以包括美学工作者的努力。过去三四十年以来,美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基督教成为人们生活的精神支柱;而在中国,宗教并没有起到这种作用。因此,我们有人认为在中国美学实际上取代了宗教。今年在中国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意义非同小可,首先是改革开放30周年,然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们举办大量研讨会回顾和反思中国在过去30年、60年中发生的变化。在考察中国美学发展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美学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同西方有很大不同,我们则更侧重思辨性研究,从观点到观点,从书本到书本;而西方学者更多地进行实证研究,比如说人类学研究。能不能就此对我们提出一些建议?
本尼特您提到在中国有“美学代宗教”的情况我很感兴趣,因为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美学讨论在英国兴起的时候,实际上同它具有代替宗教而成为调节社会秩序另一种工具的可能性有某种关系,当时的社会条件是英国王权在英国内战后急剧削弱,同时更重要的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是一个市场经济在英国第一次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原先调节社会秩序和社会区分的各种传统形式趋于瓦解,因此美学为组织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途径。那个时期,美学理论和实践作为对牧师和国王权威的一种挑战,成为提高土地贵族(the landed gentry)社会地位的一种新途径,这些贵族们以其精细的审美判断和鉴别力,通过一种专门的政权行使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美学同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这种渊源构成西方历史上美学理论和实践社会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与此相反,另一方面,美学在历史上也曾作为获得解放的形式和资源而被称为反对政治权力的力量源泉。我认为这些说法需要审慎对待,应将由美学帮助构建的各种自由理解为独特的自我管理形式,理解为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自由实现治理的若干具体方式,
这些观点也许可以为具体考察现时中国美学作用提供一些颇有意思的途径。我不大了解中国儒教、佛教和道教的历史,不大了解这些教派在中国社会秩序组织过程中的作用同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秩序组织过程中的作用之间有何区别,也不大了解这些教派同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的关系以及同国民党时期和共产党时期的关系。但就现时中国美学的社会作用而言,可能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回答,一是根据福柯关于政党治理形式的概念,美学同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形式之间有何关系?二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并向全球化进程开放的条件下,美学发挥的作用是什么?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学者们真正做一些实证研究,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
福柯的理论可以为解答这两个问题提供一个思路。由此我想到了他关于存在美学的论述。尽管存在美学并不局限于艺术,但也研究艺术问题,比如艺术实践可以作为一种自由空间在组织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因为它可以为日常生活创造一整套摆脱由道德或认识论权威引领的自我塑造实践。那么,这种创造性实践的创新空间如何随着中国的文化商业化浪潮而开启、又如何同执政党的治理理念相提并论呢?
同时也可以运用布尔迪厄的理论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研究这种发展如何导致各种新的不平等,尤其是中产阶级规模急剧增长、消费能力大大提高,其消费模式不但在中国国内起着关键性作用,而且还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这些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很多同西方中产阶级类似,比如对汽车、媒体和家用电器的需求等等,同时他们对各种文化产品的需求亦趋于增长。在中产阶级出现和发展过程中,各种新的文化消费方式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否像布尔迪厄所说的那样,依赖于文化资本的获取和跨代传承机制?您刚才提到中国学界如何运用实证方法从而使美学研究超越从观点到观点的模式,我想布尔迪厄的理论正好能够为我们考察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中国成长中的中产阶级是如何获得赖以巩固和发展其特权的必要条件的?在中产阶级、执政党、市场和教育体制的复杂关系中,中国的特权和不平等现象是如何产生和延续的?研究这些问题,都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
徐方赋这个建议很有意义,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朝这方面努力。我们希望别让您太累。但下面的问题相信您同样会感兴趣。您知道,王教授在审美人类学研究方面很有造诣。他曾经带领一个研究团队深入到中国西南偏远地区的黑衣壮族聚居区进行人类学调查,带回了大量照片,反映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展示照片):住房、传统织布机、驱邪(跳大神)仪式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处于一种很原始(primitive)的状态,具体地说,他们仍生活在青铜器和新石器时代。但另一方面,离黑衣壮聚居区不远的南宁,却是一个相当现代化的城市。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宣传和发展当地经济,南宁每年举办规模盛大的国际民歌节。王教授就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名黑衣壮的年轻女歌手,在民歌节上一唱走红,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几乎目不识丁;但她的美丽歌喉和良好天赋吸引了很多人,有人主动提出资助她上学,直到大学毕业。令王教授不解的是,这位女歌手谢绝了所有资助,跑到广州打工去了。对此,王教授很不明白这个女孩的选择;从那以后,王教授就一直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像黑衣壮这样的少数民族如何能够实现现代化?他们的习惯如何能够得到改造?另外,王教授带领的这个研究小组还注意到,政府为了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状况,每年向该地区注入很多资金,但大部分钱都被用在了日常消费中、而没有用到生产活动中,这一现象同样让我们思考如何改变少数民族居民的习惯?这种文化改造的内在驱动力是什么?
本尼特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分析起来难度很大。首先恐怕是措辞或者表述的问题。
徐方赋对不起呵。
本尼特不是说您的翻译有毛病,我是说在谈论其他文化时一般都会碰到的困难,即“primitive”这个说法可能会引发的影响。我近期关于博物馆的研究课题中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西方人类学的历史及其同殖民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显然,用“primitive”来描述殖民地居民的文化并在博物馆中按照这一观念展示其文化够成了殖民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早期西方人类学的这种倾向,从20世纪初谱之•博厄斯(Franz Boas)创立人类学开始,到整个20世纪乃至进入21世纪人类学大发展,一直受到学界内部的批判。所以用“primitive”来描述其他民族,即使曾经有过,也是很少的。
徐方赋您是说这个词本身让人生厌?
本尼特是的,但不光是令人生厌的问题。根本问题在于将其他民族的人说成“原始”这个观念本身遭到强烈反对,因为这个观念表明从“原始”到“文明”似乎只有一条路。目前普遍接受的观念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不能单纯按照发展的时序加以分析。不同文化的发展可以根据其自身的情况和水平选择不同的道路,承认文化发展多元性而不只是将不同文化按照等级次序进行排列是当前西方人类学的主要特征。我可以用一个具体事例来说明这一点。你们知道,我曾经于80年代和90年代生活和工作在澳大利亚,而且几个月后我将回到那里工作和生活。诚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曾经令人遗憾地将澳洲土著居民看作不但是原始的、而且是所有民族中最原始的人群。但如果现在还有人将澳洲土著居民称为原始人群,他们的愤怒和震惊程度会超出你的想象。澳洲土著居民曾经进行漫长的斗争,反对将他们称作原始人群,他们认为这是殖民者的观念。土著居民的抗争和信念无疑是正确的,西方人类学工作者也基本上接受了这一事实,因为一个民族技术发展水平较低并不能说明他们的信仰体系、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水平同样较低。
所以说,如果“原始”是一个措辞和表述的问题,则这种表述反映出一个深层观念问题。因此我想说,您的问题可以用不同方式加以表述,相信王教授也是这个意思。我想采用的表述方式是:在少数民族受到多数民族统治的语境中,涉及到两者关系时,如何提出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好做一般性的回答,我只能说重要的是应该区分不同的发展方式。回到澳洲土著居民地位的问题上来,在外族统治的背景下,我们讨论其发展问题时,需十分清楚发展的内容是什么。整个澳洲土著居民、尤其是澳洲内陆地区土著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他们的寿命同白人的差距可达20年;同其他澳洲居民相比,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住房状况、卫生条件、受教育水平等等要差很多很多。所以改善物质生活确实是这些居民的实际问题,但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不能离开土著居民受澳洲政府统治的基本史实,而且实际上这样的历史仍在延续。
徐方赋但我们刚刚说到的黑衣壮族居民同您说的澳洲土著居民情况稍有不同,他们并没有像澳洲土著居民受到外族入侵和统治,他们只是同外界隔绝。
本尼特是啊,我刚才也说到,我对您说的这个民族的历史不了解,所以无法针对这个具体问题提出我的意见。不过我的基本看法是我们在提出某一人群的习惯比较落后因而需要加以改变等类似观点时,必须十分谨慎。毫无疑问(所有社会人群都是如此),如果政府欲实现若干具体目标,则相应的具体习惯需要得以改变:比如垃圾管理和降低温室效应等等。但此类规划不等于说我们需要改变某些特定人群的所有习惯。而且(我想同样适用于王教授研究黑衣壮居民),如果不深入了解和尊重边缘化民族的信仰、了解和尊重他们坚持自身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的权利,这些民族的生产关系无论如何都得不到发展。再有,我清醒地认识到,澳洲土著居民生活中关于“黄金时代”的宇宙神话和实践活动对于他们在漫长而痛苦的殖民统治历史中保持其独特的身份和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西方人类学家们一开始将这种“黄金时代”活动看作一种原始的信仰体系,认为其不够精细,称不上宗教,因而予以否认。但后来,由于土著居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进行了激烈斗争,“黄金时代”活动逐渐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复杂性和完整性的知识体系,一种同西方宗教一样发达的宇宙哲学。回顾一下历史,土著居民对殖民者反驳道:“你们来到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对黄金时代和祖先的信仰是一个原始的信仰体系,但同时你们又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通过“无沾成胎”诞生的(an Immaculate conception),谁傻呀?凭什么说我们的信仰就比你们的更为原始或者更不可信呢?在我们看来,你们的耶稣基督说才不可信呢!你们的神话同我们的神话有什么不同吗?
所以我认为关于一个民族的习惯是原始的或者落后的说法、关于如果这些民族要发展就必须根本改变其习惯的说法不会产生多大作用。但与此同时,正如王教授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我也认识到改善边缘化人群物质生活的社会和政治努力有时候会劳而无功,令人无奈和伤心,这不是因为这些人群的习惯问题,而是他们经常用来将外力拒之门外的一种反抗方式,是他们逆反心理的一种表现。这种反抗和逆反心理使政府处于无奈,各种援助项目,无论是资金援助还是物资援助,经常无法真正改善当地状况,其真正原因在于这些受援人群没有走出他们试图走出的历史阴影。
王杰是啊,这个问题十分复杂,需要作进一步探讨,我也准备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然后和您继续交流。接下来我们讨论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您在前天晚上的报告和昨天的研讨会上都提到你对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解和特里•伊格尔顿有所不同,能否具体谈谈?
本尼特好的。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伊格尔顿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福柯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差异,或者至少是同我所诠释的福柯方法论的区别,我曾经提到,这个方法论有时候也意味着以福柯反福柯(Foucault-contra-Foucault)。来南京前我从近期《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上看到了你们两位对特里•伊格尔顿的访谈录,注意到在访谈中特里•伊格尔顿提到他依然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徐方赋顺便问一下,您对自己的看法,您是否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本尼特不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要是那么说显得有些傻,因为我的研究对马克思思想的很多方面都提出了批评,所以如果我那么说叫人无法相信。不过另一方面,我确实受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很大影响,但我不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来追求,因为面对当今许许多多社会和文化矛盾,如性别问题、性问题、宗教问题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显得僵化、囿于19世纪的观念,因而无法对这些问题加以充分分析。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遭到很多强烈批评,如女性主义学者、种族和民族学领域的学生,像福柯、德勒兹这样的学术流派等等,都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仍然是我们分析阶级和资本主义动态等问题的重要理论源泉。所以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在现时社会中没有学术价值,只是光有马克思主义远远不够,在很多无法运用阶级理论进行分析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可资我们参考的东西不多。
您说得对,特里•伊格尔顿确实将自己的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当中,他将审美作为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对西方美学发展史上若干关键时期研究的许多见解都很深刻、能够激发人们思考,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伊格尔顿的著述中学到很多东西。我的不同意见集中在他进行理论研究的视角上。他的“审美意识形态”主要有两个观点。一方面,伊格尔顿试图说明审美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作为一种知性实践,审美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通过泛化,将资产阶级的一整套价值观和自我塑造(self formation)实践掩盖起来、隐藏起来,审美同其他任何意识形态一样产生了一种特殊主体,这些主体往往错误地认识自身和真实历史的关系(根源于生产关系),这种错误认识并进而错误地泛化了资产阶级价值观。这是美学的消极方面。而另一方面,伊格尔顿则试图说明美学作为一种反意识形态孕育了解放的预言。从这一思路出发,在伊格尔顿的描述中,一方面,历史上美学是传递并同时掩盖某些阶级和性别权力的机制,另一方面美学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人类成长过程中的价值观念——有可能为反对和批判现有统治形式的各种社会活动所接受。这些观点当然有其正确的一面。后康德美学理论无疑影响了马克思关于历史进程成为推动人类实现潜能的观点,此类观点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文化实践活动。但这些实践活动实际上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较少,更多地则是受到后康德理论的影响,比如后康德理论中关于艺术和自由关系的论述对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美学理论和工艺美术运动(4)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作为挣脱工厂制度奴役的一种武器曾经同工人们日常生活中为获取自由进行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曾经为英国工人阶级这方面的知性生活进行十分动人的描述。但我始终认为你不能用一套自相矛盾的概念——即美学既反映了资产阶级价值观、又预言了工人阶级的解放——来讨论美学理论在任何条件下对于决定文化和艺术实践效果所发挥的作用。
所以我认为这是伊格尔顿观点中最大的弱点,因为这意味着他无论研究哪个阶段的美学史都要运用这个矛盾来得出几乎相同的论点。关于美学始终为这一基本矛盾所左右的观点意味着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看到这对矛盾在起作用,因而这种观点最终将成为一种无视历史的观点(a non-historical form of analysis)。结果是,伊格尔顿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没有历史观点,而成了口头唯物主义。在我看来,这就是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的重大缺陷。在探索意识形态矛盾如何在历史长河不同阶段中的不同表现时,他的眼光只集中于这一矛盾的一般方面,而没有仔细考察美学理论同具体历史条件下具体社会和物质机构相联系的不同途径。
简言之,我认为伊格尔顿的方法过于强调美学的历史由某个一般性理论框架所支配,而且太过于在观点层次上做文章,他很少超越最好称之为哲学史观的一般层次而深入考察在不同背景下美学得以实质参与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关系。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运用福柯的视角分析美学早期历史的文学史家如玛丽•普维(Mary Poovey)的著作,就不难发现在关于美学、市场社会发展和早期自由政府形式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中,这些文学史家的分析要比伊格尔顿的分析更有洞察力、更有历史差异性。福柯理论的魅力在于它允许、或者说要求研究者提出研究历史的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福柯的观点有一定作用,他将历史重新界定为一个一脉相承的系统工程,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研究现在,用新的方法来揭示历史的问题和走向,而不是将历史看成一个从源头走来而一成不变的过程。而伊格尔顿关于审美即意识形态的观点恰恰遵循了追寻源头矛盾的逻辑。
王杰十分感谢您的分析和评述,我想这些意见对中国学者的思考和研究很有启发。虽然我们还有问题要探讨,但下午您还有工作,所以我们的访谈只能先到这里。谢谢。
本尼特不客气。很高兴跟您探讨这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您的研究对我同样很有启发。英文题目及作者:“Aesthetics, Society, Politics”—An Interview with Tony BennettBy Wang Jie and Xu Fangfu
(1)原文为the working-class culture of the necessary,Tony Bennett解释,即由其经济必然地位所决定的必然文化品位。
(2)原文the social:Tony Bennett提供了福柯的定义,指为谋求某一群体人们的福祉和社会保障而应该加以组织的社会行为。
(3)Elgin Marbles,大英博物馆所藏古希腊大理石雕刻。
(4)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又称“手工艺运动”或“自由建筑运动”,代表人物是拉斯金和莫里斯。